《十首歌里的摇滚史》:一首歌跨越几个时代
来源:现代快报|2016-12-30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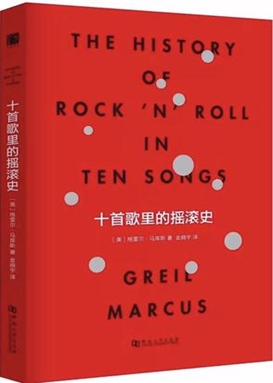
《十首歌里的摇滚史》 [美]格雷尔·马库斯 金晓宇 河南大学出版社
鲍勃·迪伦获得诺奖,带动了有关迪伦书籍的销售,包括他的各种传记,与他相关、不相关的摇滚史,以及其他泛摇滚文字。
《十首歌里的摇滚史》是其中的一本,上个月刚刚出版,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摇滚乐评人、文化研究者格雷尔·马库斯。读过《聆听大门》和其他音乐评论文字的人,会对他有个基本的了解。他应该是一个不无另类、有点高冷的人。他的文字和想象力,个性十足。
在这本书中,马库斯完全打破了以往摇滚史中的编年体例,选取了1956-2008年之间的十首摇滚歌曲,以独特的细腻笔触和他对音乐与历史的庞大知识积累,深究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:一首歌曲的诞生,歌曲的不同版本、演唱和演绎方法甚至不同艺术形态的演变,其背后的深刻文化意义、社会文化风向的变迁、音乐产业的变革等等。
在格雷尔·马库斯看来,即便是一首不出名的摇滚歌曲,也会以它自己的方式来讲述摇滚的故事和历史。
不寻常地构建历史
鲍勃·迪伦获奖以前,甚至在网络风行之前,在中国就有许多有关摇滚乐历史的著作。虽然国内的作者不乏“国外资料剪刀手”之嫌,但是那些资料在他们的妙手组织下,倒也成了像模像样的摇滚乐入门书。几乎所有的摇滚史书写,包括国外作家的作品,都是依着时间的顺序,叙述摇滚乐的发展变迁。也许是因为摇滚乐的历史并不漫长,几乎就是当代史的一部分,所以书写者对其中的重要节点、重要人物、重要作品的认识也大同小异。一本摇滚乐史的好坏,大家拼的是资料的丰富与否,和文字是否好看和抓人。
《十首歌里的摇滚史》,如果你不看介绍,很可能以为作者会选择摇滚历程中十首最重要的歌曲,诸如迪伦的《像一块滚石》、披头士的《佩珀军士孤独心俱乐部》等经典,通过对它们独特的创作经历、标志性的演出,以及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的描绘,构成某种具有象征性的历史意境。这是很传统的写法。但是在格雷尔·马库斯那里,“摇滚乐正式、权威的历史是真实的,但它不是全部的真相,它根本不是真相。它是一个杜撰的故事,传播得如此广泛,以至于人们相信它,但它不符合他们的真实感受,它甚至可能扭曲和压抑他们的感受”。马库斯引用一位音乐剧作家丹尼斯·波特的话,来加强他对摇滚史的认识——“我认为我们的肩膀上边都有一个小剧院,在那里,过去和现在,我们的抱负和记忆,简单而无情地混合在一起”。
在他看来,一张唱片即使没有进入所谓的历史,但是在排行榜或某个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淡淡的痕迹,这也许比将它们排除在外的任何宏大叙事更有价值。简单地说,一首歌的好坏不在于它是否进入了所谓历史,而在于它是否打动了你,进入了你的记忆。
很显然,这本书所选择的十首歌,是打动格雷尔·马库斯的十首歌。如果你相信他的品位,那么这本书不会让人失望,即便它那么离经叛道,不走寻常路。
一首歌跨越好几个时代
提起巴迪·霍利,现在很少有人知道,这位在1959年2月,22岁时死于飞机失事的年轻人,是美国摇滚乐的早期代表人物。他的音乐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两大乐队——披头士和滚石。霍利虽然年轻,但是创作并演唱了很多热门摇滚歌曲。《哭泣,等待,希望》是其中的一首。很奇怪它并不是最有名的,但却是格雷尔·马库斯最待见的。
和美国其他的文化学者一样,比如撰写美国上世纪60年代文化的迪克斯坦,他们的严肃作品不是那种死板的编年史、大事记,而是把自己的生活带进历史,自己就是历史的一部分,格雷尔·马库斯是这样带出这首歌的——“2013年的一天早晨,我走进加州奥克兰的“科尔咖啡馆”。他们平时播放的音乐很逗趣,声音总是很轻……这一天的音乐照旧模糊而遥远……显而易见,是披头士在演唱巴迪·霍利的《哭泣,等待,希望》”。
正像前面写的,这首歌并不是巴迪·霍利的代表作,但是格雷尔·马库斯选择了它。之所以是这首歌,而不是别的作品,是因为披头士选择了它,而且是在10年后的1969年。这样,这首歌就很自然地串联起了近十年的时光,同时把巴迪·霍利和披头士简短而感性的散文式传记贡献给了读者。而且作为历史,在一些貌似平常的场景中,格雷尔·马库斯很巧妙地植入了诸如猫王、迪伦等经典时代符号。
同样的方法用在了《我唯有哭泣》上,这首歌是埃塔·詹姆斯22岁时的作品。那是在1960年,埃塔·詹姆斯虽然只有22岁,但是演唱起来“像活了十几辈子,而且记得里面的全部事情”。格雷尔·马库斯对她的演唱称赞有加,“当她歌唱的时候,她的整个人生,她的未来还有她的过去,似乎在她的眼神后面浮动”。而格雷尔·马库斯之所以要写这首歌,是为了另外一个更有名的歌手的出场——碧昂斯·诺尔斯在2008年上映的一部电影《卡迪拉克唱片》中扮演埃塔·詹姆斯,并且重新演绎这首《我唯有哭泣》。可能是碧昂斯更为当代和鲜活,格雷尔·马库斯用更多的篇幅跳出这首歌,详细描绘了她参加奥巴马第二次就职典礼,以及美国棒球超级碗时演唱的情景。在他看来,碧昂斯就是一个鲜活的神话。
不仅是写同一首歌,不同时代的人演唱,格雷尔·马库斯还把两首同样是写金钱的歌曲,放在同一章节里描述,贝里·戈迪的《金钱,这是我想要的》和披头士的《金钱改变一切》。而这两首歌的内涵远远不止于摇滚,它还涉及到美国文化,美国人对金钱的认识和态度。
在历史中植入情感
“他激情四溢的文字就如同他所热爱的音乐一样包罗万象。”这是著名作家拉什迪对格雷尔·马库斯的评价,而熟悉他的读者,也会因为他独特的视角和充满想象力的文字,对他的新作有所期待。
可能是热爱音乐,特别是摇滚的缘故,在格雷尔·马库斯的笔下,语言就像音符一样自由自在。就这本《十首歌里的摇滚史》而言,你可以把它当作严肃的音乐评论来看,也可以当作好看的文化散文来读。每一个歌手都有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时代,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背景,每一首歌都是这个时代下的蛋。它确实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严谨的摇滚史,你也无法通过它了解摇滚的发展脉络,但是就像格雷尔·马库斯说的,有的时候,一首歌就见证和体现了历史。
格雷尔·马库斯的另一个特点是,他不会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和真实,而把文字搞得冷冰冰的。他不喜欢零度叙述,他喜欢倾注感情。在写《哭泣,等待,希望》这一章时,很显然格雷尔·马库斯对巴迪·霍利的早逝感到惋惜。霍利死于1959年,但格雷尔·马库斯却想象,他在1960年挤在观众席中去观看民歌手卡洛琳·赫斯特的表演,因为1957年在克洛维斯的一个录音棚里,他曾为她伴奏;“不久以后,你能看见鲍勃·迪伦站在人群的后面看见霍利——霍利进来的那一刻,迪伦已经注意到他了——他站起来唱《永不消逝》”。
格雷尔·马库斯也在书中加入更多的人性,一些小温暖,在《我唯有哭泣》这一章最后,他不无调侃地写道,“埃塔·詹姆斯于2012年逝世,享年七十三岁,除了其他许多事情之外,曾让她愤愤不平的是,2009年在奥巴马第一次就职舞会上受邀演唱《终于》的是碧昂斯而不是她自己”。
这最后一句,多半是出于虚构,但是放在结尾有一种时间流逝的感觉,温暖而不刻薄。
在格雷尔·马库斯看来,即便是一首不出名的摇滚歌曲,也会以它自己的方式来讲述摇滚的故事和历史。

- 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“中老年之家”微信公众号(免费)
- 中老年之家www.zlnzj.com以服务广大中老年群体为己任,每天提供海量的养生、娱乐、政策、爱好、潮流等中老年资讯,集文字、视频、图片等诸多形式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老年门户网站。网站拥有同名微信公众号“中老年之家”,并提供手机端浏览网站的功能,让您随时随地掌上获取最新中老年资讯。
相关阅读
- 《十首歌里的摇滚史》:一首歌跨越几个时代2016-12-30
- 被嘲笑过的梦想,总有一天会让你闪闪发光2016-12-29
-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:巨变时代的知识分子2016-12-29
-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:近代知识分子重塑秩序2016-12-29
视频点播
养生小贴士更多>>
- 老人经常咳嗽不是小事,四种咳嗽要重视
- 早晨这样喝第一杯水,从来不担心肠胃会
- 为什么老得快?13个坏习惯加速衰老
- 它能保全家健康!很多人只知道它的一种
- 看耳知寿命摸耳治百病,教您十步揉耳保
- 起床后5个不好的现象,说明你越来越老了
- 早餐决定寿命长短,日常4个小动作能增寿
- 老人总是失眠?告诉你摆脱的失眠的几个
娱乐播报更多>>
- 陈凯歌《妖猫传》定档2017年12月22日
- 蔡国庆《爸爸去哪儿4》称老婆很贤惠 计
- 撒貝寧評董卿首任制作人:她極有勇氣
- 刘晓庆空降“女王盛宴”,《武则天》今晚
- 今晚《养生厨房》播出 菜名:五彩鸭肉
- 今晚《养生堂》播出《名医夫妻话养生
- 《我是大医生》白斑,可能预示着癌前病
- 12.29《星光大道》要为大家讨福利,送福



 2016-12-08
2016-12-08
 2016-12-28
2016-12-28
 2016-11-14
2016-11-14
 2016-12-03
2016-12-03
 2016-12-28
2016-12-28
 2016-12-29
2016-12-29


 64岁失独高龄产妇生下7斤4两男婴
64岁失独高龄产妇生下7斤4两男婴 奖章被盗劳模抹泪:那是我命根子
奖章被盗劳模抹泪:那是我命根子 女子下班遭陌生男尾随,被摁倒在地
女子下班遭陌生男尾随,被摁倒在地 落日余晖下 颐和园现“金光穿洞”
落日余晖下 颐和园现“金光穿洞”